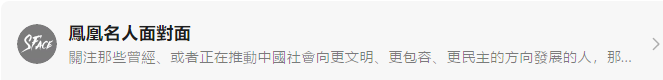以下文章来源于鳳凰名人面對面 ,作者名人面对面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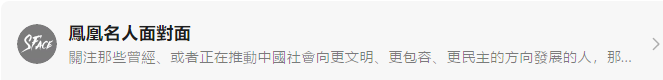

在距离广州市区一小时车程,有一座特别的农场---慧灵农场。
对于一群人来说,在慧灵农场里做做农活、喂喂小动物,不只是“田园牧歌”,更是一种治疗的手段。
在医学上,他们有着和常人不一样的特质,智力发育迟缓、自闭症、唐氏综合征、脑瘫等,被统称为心智障碍者。

孟维娜,是这一群心智障碍人士的“大家长”,中国慧灵的创始人。在30多年前,她在广州创立了中国第一所民办特殊教育学校,决心帮助智障人士过上更好的生活。在心智障碍服务行业,慧灵是中国成立最早、规模最大的草根机构,也被看做是行业的风向标。“残障问题是全人类的必然性,在少数人身上发生了,比如说它的绝对数字是10%,我们是分母,他们是分子,这个分子是从哪里来的?是从分母里来的,那10%他们承担不了,肯定是个灾难。我们广州市前年一个老太太,把一个四十多岁的瘫痪儿子亲手砍死了。那她首先要意识到,她是错的,但是为什么她要这么做?社会没能来解决这个负担。”在中国,针对心智障碍群体的服务机构有4000多家,服务人数超过20人的只有大约三分之一,超过50人的就更少了。而孟维娜创立的慧灵,在中国有38个服务点,服务着大约2000人,也是中国最大规模的心智障碍服务机构。

“为什么我要发展呢,别人会认为我很有野心,其实我觉得不是野心起作用,是因为很多人来找,你自然而然就顺着那个需求,要去做这个事情。”
在镜头前,孟维娜和学员们一起做农活,喂小动物,多少有些不自在。随着慧灵的扩张,她经常在不同城市飞来飞去,和学员们的相处时间也变少了。和他们在一起,孟维娜依旧保持着直性子,相比于传统“慈母”那样的陪伴和照顾,她似乎更擅长,面对和处理一些更复杂的难题。“我们都觉得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场地问题。哪一天拆迁了,哪一天房东说市场价调高了,你说搬就得搬。残联这么多地方都是空的,我们又交这么贵的租金去租私人的地方,还可能流离失所。那为什么残联不可以开放给社会组织一起来做呢?”

“说老实话,政府投入到民生真的用了很多钱。他们自己不是不想做,而是想做却没有想出什么方法来。但民间已经取得了一些经验,你只要把这个体制和壁垒打开,对接起来,起码就很顺理成章了。当然现在也开始改革,但是缓慢得不得了。按照这个社会制度的流程,人的生命就浪费了,甚至已经死去了。在这种情况下,你就得赶紧去做事情。”目前,中国民间针对心智障碍服务机构的创办人,大多是孩子家长,也主要围绕着自己孩子的需求来展开服务。而孟维娜带着慧灵,做了很多别人不敢做的大胆尝试,她在中国第一个开展了针对成年人的服务,38个城市的78个社区中,建立了“社区家庭”,让心智障碍群体回归社区。她又在争议中开展了托孤式的终身托养服务,跟26位家长签订了协议,承诺在家长走了之后,为这一些学员们养老送终。这一路跌跌撞撞,慧灵业发展得越来越庞大,而孟维娜也成为社会服务领域的“先行者”。然而,最初创立慧灵的她,并不是这个领域的专业人士,她甚至不知道慈善是什么。

“都说三十而立,三十岁的时候,我不知道哪里有出路,要做什么,觉得对不起祖宗,对不起自己,每天喘不过气来,很压抑,觉得我再不做一个事情,我就宁愿去死。在这个时候,我就看到了德兰修女的事迹,是比豆腐块还小的一个消息。我对修女到底是什么也不知道,反正就是知道,她在印度做了一个仁爱之家,做残疾、临终关怀这些。同时期就是邓朴方的事迹,他开始办残疾人的福利基金会。”
孟维娜看了邓小平的儿子看邓朴方的传记,主动找到他,表示自己愿意跟随做残疾人的服务。在朋友的帮忙下,孟维娜从一位老军医那里,拿到了500位残疾孩子家长的联系方式,她又开始做自己最擅长的事——给家长写信,留下自己的地址,和家长们相约见面。一转眼,在信中和家长相约见面的日子到了。而那一天,寄出去的500封信,给她带回了300个人。“自己没有想到,无知当无畏了,你好像什么都没准备,来了这么多人。好在同时进行了很多的事情,香港一方面也有回应了,来了十几个机构,把这几百人集合在一起。他们就一个个评估给我分类。就留下了智力障碍的,就你只能做这一个。”
北京慧灵朝阳组社区家庭里的学员,在自己家里过完周末,每到周一,都会被送来这里,开启一周的住宿生活。
每周的开会讨论时间,他们都要为接下来的几天,安排上自己想做的活动。
而点名、值日、做饭这些日常,是每个人都要为这个共同的“家”付出的劳动。
用高墙和铁门把心智障碍者隔离起来,单独照顾、这是中国特殊教育学校的普遍操作。九十年代初,慧灵刚刚成立的时候,也采取过类似的方式。而随着更多的出国学习、吸取经验,孟维娜决心要改变心智障碍者集体居住的模式,希望让他们回到社区,和大家一样在社区里正常生活。她在普通社区里设立“社区家庭”,由“生活辅导员”带着几个心智障碍者组成“家庭”,训练他们独立在社区生活。而这种模式,也成为了慧灵在众多社会服务机构中最特别之处。

“政府对我们是很警惕的。他觉得你是一个机构,如果你是一个机构,不管你是什么家庭模式,必须按照消防措施规定,把家里变成两个门,我们做不到,因为那个房子是租的。他们也不愿意我们是双层的床,我们也不喜欢双层的床,但是你的成本压在那里。后来我们就通过这个所谓的经历,总结出以后租房子,就去租家长的房子,因为他是房东,又是家长,比我们机构和他硬碰要好很多了。”事实上,日益发展壮大中的慧灵,一直经历着成长的阵痛。孩子一多,各种各样的难题就来了,除了常面临的资金问题、场地问题,而最难面对的是各种意外。从业30多年,因为学员发生事故,她四次站在了法院的被告席。尽管存在着潜在风险,她还是坚持,“坚决不能因为1%的风险而放弃99%的自由。”2000年,孟维娜把慧灵从广州开到了北京,自己也搬回来了北京。
可刚来不久,位于北京方庄的社区就收到了投诉,住户们找到了物业,控诉慧灵带来的10个孩子“精神有问题”“对别的住户有潜在威胁”等等。而孟维娜极力解释,但是物业也无能为力,慧灵只能“搬家”。新小区里,她做了大量调研,提前和邻居打好招呼,在搬来之后,主动帮社区铲除小广告、打扫街道、清理生活垃圾,逢年过节也主动向邻居们送出孩子们自制的小点心,还有在小区挂出海报,让邻居们也了解心智障碍的知识。在那之后,北京范围之内投诉的情况几乎没有了。

“关于残疾人的保障法,我们在2004年的时候就提出来,要做修改。我们就觉得‘保障’这个字眼太落后了,希望还是从‘权利’的这个角度,虽然法律的名字没有改,但是条文里也确实往‘权利’倾斜了,拧过来一些了。但实际上整个来讲还是比较保守的。”
“除了残障是一个主体,整个社会都必须要变成一个主体。不然的话,它永远都是把人分成所谓正常和非正常。比如说无障碍设施,我们总觉得好像是为很小一部分肢体伤残人士设置的,但是后来发现即使不是残障人士,如果拖着行李要上台阶,也觉得很累。”

“全社会都应该付出、参与,也享受,残障问题在其中就自然而然得到解脱,如果我们一直强调这是残障人,潜意识里因为你是少数,换成我来帮助你,就好像还是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。如果成为全社会的权利和义务,这个问题就变得自然而然了。”